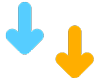邢台东石门“这有园”里,父母种下的是菜,收获的是时光
- 2026-02-10 00:49:20
父母从乡下搬来城里已有数年,住高层,电梯上上下下,阳台种过几盆蒜苗、几丛小葱,到底不成气候。
母亲常站在窗前,望着楼下水泥地发呆。父亲则背着手,在客厅踱来踱去,脚步丈量着不存在的田埂。
直到媳妇在“这有园”租下一块地。园名“这有园”三字朴素如泥土,位置在离家八里的东石门村,对于交通方便的现在社会来说不算远。
园子面积七十平米,说大不大,在农民眼里,却是一整个世界。父母第一次去看地时,正是春分。父亲蹲下身,抓起一把土,在指间捻了捻,眼睛忽然亮了:“这土,可沾。”
接下来的每个周末,成了全家固定的归田日。
父亲为了方便,特意购置了一辆三轮车。开上三轮,带着种子、农具和攒了一周的雨水预报。那块地被他们规划得如同军事地图——东南角阳光最好,种西红柿;西北角稍阴,栽韭菜;中间起垄,茄子青椒各半;边边角角,撒了香菜和小葱。
父亲的手重新握起锄头时,我看见了某种复苏。那双手在城里拿遥控器、提购物袋时总是垂着,此刻却有了向上的力量。一锄下去,土地翻开深褐的波浪,新鲜的土腥味漫上来,那是他们呼吸了一辈子的味道。
母亲蹲在地里移苗,动作缓慢而精确。每一株苗栽下去,她都轻轻按实周围的土,像是在给婴儿掖被角。我问她累不累,她抬头笑笑:“这算啥累?心里可得劲儿嘞。”
夏天来到时,菜园绿成了一片海。西红柿挂起红灯笼,茄子紫得发亮,豆角沿着竹架攀成绿色的瀑布。每个周末,我们都带回满篮的收获。邻居见了问:“菜市场买的?”母亲总是骄傲地说:“自己种的,没打药,吃着放心。”
真正的丰饶是在秋天。
当城里人开始讨论哪家生鲜配送最快时,父母的菜园正进入最慷慨的季节。大白菜卷起紧实的心,白萝卜半截身子拱出土,胡萝卜的缨子绿得晃眼。还有蔓菁——这种城里少见的根茎,在父母的记忆里,是冬天的信物。
霜降前后,父母开始最后的收获。白菜砍下,晾在田埂上;白萝卜和胡萝卜装进编织袋;蔓菁连根拔起,抖落泥土,露出淡紫色的皮。那天下午,阳光斜斜地照着,父母坐在地头整理收成,身影拉得很长很长,像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两棵老树。
入冬后第一场雪落下时,母亲端出了豆沫汤。
那是西部山区世代相传的吃法。黄豆泡软,磨成粗沫——在城里只能用磨好的黄豆面代替,慢火熬成乳白的汤底。汤里煮着自己种的蔓菁、北瓜、胡萝卜,咕嘟咕嘟的汤里冒着热气,满屋子都是清香的蔓菁味儿。最关键的是那一筷子“酸黄菜”——母亲把蔓菁嫩叶洗净,用粗盐揉了,封在陶罐里发酵月余而成。青叶已成金黄,酸香扑鼻。
一碗下肚,暖意从胃里扩散到四肢百骸。父亲喝得额角冒汗,忽然说:“这味儿,跟我小时候老家的一模一样。”
我忽然明白了。父母租种的从来不是一块地,而是一段可以触摸的时光。
在“这有园”的四季轮回中,他们找回了与自己、与土地、与记忆的连接。那些西红柿的酸甜、白菜的清甜、蔓菁的甘甜,最后都化作一碗豆沫汤的醇厚,熨帖着被城市生活褶皱的灵魂。
窗外的雪越下越大,覆盖了高楼、街道和匆匆的车流。而我们的屋里,一碗豆沫汤的热气正缓缓上升,里面沉浮着整片土地的馈赠,和一个不再漂泊的冬天。
好文推荐
魅力太行 · 宁儿 ‖ 北京游记之海淀公园
魅力太行 · 宁儿 ‖ 北京游记之人定湖公园
魅力太行 · 宁儿 ‖ 北京中山公园游记
魅力太行 · 宁儿 ‖ 北京之奥林匹克公园
魅力太行 · 宁儿 ‖ 北京海棠公园游记
魅力太行 · 宁儿 ‖ 邢台历史文化公园散记
魅力太行 · 宁儿 ‖ 北京园博园游记
魅力太行 · 宁儿 ‖ 北京大栅栏游记
魅力太行 · 宁儿 ‖ 北京地坛公园游记
魅力太行· 宁儿 ‖ 北京后海游记
魅力太行 · 宁儿 ‖ 北京游记之烂漫胡同
魅力太行 · 宁儿 ‖ 北京游记之徐悲鸿纪念馆
北京中山公园秋游记:赏秋叶,品历史,享宁静
邢台达活泉公园冬日之约:重拾那些被遗忘的美好记忆
冬至的饺子,抵不过娘的生日:漂泊四年,我终于读懂“孝”的重量
北京游记之南锣鼓巷
北京游记之潘家园
宁儿游记之北京月坛公园
北京游记之模式口驼铃古道
魅力太行 ‖ 北京游记之雕塑公园
魅力太行 ‖ 北京游记之王府井步行街
魅力太行 · 宁儿 ‖ 北京游记之京顺园公园